一、引言
“一个人只有远离人群,才能真正和他们在一起。”这是我在作文里最常引用的《树下的男爵》里的句子,来论述人真正的需求通常是要寻找的,以及自我标准和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联系。说起高中时期的阅读,通常都比较印象深刻,议论性作文的独特性和不可预料性决定了每一道论题都将开启一次崭新的写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论据的积累可谓是一大利器,它不仅是论点的有力支撑,有时还反向提供不少新思路和新角度。因此,读过的书,都会成为我写进作文里的素材,在我的一次次运用下,阅读过的文字以另一种形式陪伴我,似乎能够焕发出和我的某种特别关系、某种特殊连接。
说回这本书,如果有人和你说:一个人上了树一辈子不下来,请你把他的一生写下来。我相信如果没有出色的想象力,一定是无聊且荒诞的。但幸运的是,卡尔维诺用无比精巧的想象力和轻盈的写作手法,让每一位读者都好像能够洞见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个树上的世界中有历史和政治的身影,有人性真理的温暖和明亮,也有对现实与虚幻、真实和幻想边际的缝合与跨越……小说中创造的人物、故事、思想和感情与“我往哪里去?——如何过好这一生?”这一核心问题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体现了卡尔维诺在《千年畅想录》里强调的:用一种“文学的轻”来反映“现实的重”。在这本书里,“重”在如何在重重矛盾下走向自我完整。
二、背景介绍
关于上述问题的提出,离不开时代背景,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作家的写作。《树上的男爵》创作于1956—1957年,正值冷战时期,局势紧张,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苏联对卡尔维诺的镇压和意共的迎合使他在1957年退出意大利共产党。《树上的男爵》的背景则设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的启蒙思想强调理性、自由、平等,推翻封建和专制主义思想,反抗教会。卡尔维诺将自身的思考注入书中,在时代迈向更好的过程中,反思个人良知和历史进程、希望和痛苦的关系问题。《树上的男爵》同《不存在的骑士》和《分成两半的子爵》一起收录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分别代表着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争取存在与生存、从分裂到整合、矢志不渝地坚持自我、达到非个人主义的完整。但这三部曲也不仅仅指出了一条通向自由之路,也是现代人一路走来的记录,总能在其中看见历史、现代、未来中,我和我们的某些特征。
三、矛盾重重
第一重矛盾发生于出走,上树是否是真的离开?离开是否就能拥有自由?主角柯西莫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下,父亲却固守着与新思想背道而驰的思想,比如获得旧时代里公爵爵位、家族继承,与其他贵族家庭的争斗,保持着宫廷中的礼节,这些压抑着男孩的独特个性、自然性。于是,柯西莫拒绝吃下蜗牛,离开家,爬到了树上,远离地面,以此对抗父亲、对抗标准的人格塑造、对抗本性的压抑。这并不是一次赌气,而是确确实实的离开,这一场离开的原因并非树上有他执迷不悟的东西,也不是要隐居,做一个彻底的“隐士”,而是依靠激情离开了困住他的东西,选择了自由,可以说是意志独立和反叛抽象的统一化形象。矛盾的是,远离社会并不能规避自己身上的社会性。就好比选择辞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却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生计、家庭、未来……选择自由并不代表拥有自由,自由需要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相对保持和平衡。要对世界和自身处境有充分认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然和历史,自我建构和个人准则,才能获得心灵的自主性。选择了自由,也要有能力承担选择的一切后果,这不仅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他人负责。
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柯西莫的出走又非真正的离开。并非真正离开他的家庭和生活,弟弟和母亲给他送衣服、日常用品、枪,邻居女孩留下的小猎犬作为他在陆地上的助手;他也没有离开过陆地,他交朋友,唱歌,玩耍,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地去旅行;他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时代,他积极地参与地面活动。“树上”构造出一种观察的、超越的、理想的视角,与地面的一切保持距离,可以说柯西莫既保持独立又融入社会。书中也说过“如果想看清城市,就要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这种距离并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自我要求,是一个人心甘情愿给自己立下一条规则,并严格遵守,因为如果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卡尔维诺也说他并不是在写一个拥有不常规行为的年轻人的故事,不是逃离人际关系、社会生活,成为一个避世者、逃逸者、厌世者,而是一个投身一切与地面有关的运动、为大众谋求利益的人。远离他们,才能真正看清他们、走进他们、和他们在一起。
在树上的生活里,柯西莫遇到了不同的人,第二重矛盾发生在与他们的相识。柯西莫遇到了被所有人憎恶的强盗,他被认定是“恶”的代名词,但有一天这个强盗看到柯西莫在看一本书,并在他看过这本书后迷恋上了小说,以至于不愿再做强盗,但他最终还是被抓了起来判以绞刑,在临死前为不能读书而痛苦,在听见尚未看到的小说结局之后,自己踢开了梯子,走向生命尽头。书中是这么描述刑后场景的:
“当他的身体不再扭动时,人群走散了,柯西莫骑坐在吊着受绞刑者的那根树枝上,一直留到深夜。每当一直乌鸦飞来要啄食尸体的眼睛或鼻子时,柯西莫就挥动帽子将它赶开。”
擅长水利工程的律师叔叔,拥有伟大的理想:浇灌出沃土,造就美丽的果园、花园。他也把变革的愿望倾注其中,绘制了许多图纸。柯西莫以为叔叔是整个家里面离他最近的人,他也与叔叔结下了友谊,和叔叔一起试图建造水利工程帮助别人,但叔叔是一个对一切都没有耐心的人,很快,在屡屡碰壁后,他便厌倦了,反倒帮助海盗来掠夺当地居民的财产,他的形象在柯西莫心中倒塌了。
“柯西莫既有冲动跑去揭发这个奸细,保护我们商人的货物,又想到我们的父亲将要承受的痛苦,知道他对这异母兄弟有着无法解释的深情,柯西莫的心被撕裂了。”
所谓的恶是否是真的恶,善又是否是真的善,人又是否真的能判断。当一个人做出改变时,人心的评价又是否能跟着改变,强盗直至最后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重,这是令人感到惋惜和可笑的。叔叔与曾经形成巨大的落差,恩将仇报的小人行为是可恨的,也是可悲的。叔叔习惯不与别人发生关系地工作,不用顾及他人利益,因为他软弱而无绝断,从来不会反抗他人的意志,或许准确来说,他根本不会和他人相处,这提醒着柯西莫:一个人如果把命运同其他人的命运分隔开,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他成功地没有沦为同样。善恶并非绝对,人的看法不应该是刻板的、固定的。积极的改变应当被尊重,消极的堕落应该被审判。
第三种重矛盾则体现在柯西莫的爱情观上。受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所推动,作品中可以看出柯西莫对理性的热爱,但启蒙思想中理性的工具却使他在爱情中矛盾了。他的爱人薇莪拉任性娇纵,但柯西莫讨厌扭扭捏捏、矫揉造作,讨厌天然情爱表现,他充满理性的克制,尽管也在拒绝自然本性中充满痛苦,但“爱情不排斥任何东西”在他这里并不被认可。以至于嫉妒薇莪拉拥有一个比他的世界更广阔的天地,为不能独占她而疯狂。最后懊悔自己失去了她,用不正确的、愚蠢的傲气伤害了她。
大革命使柯西莫陷入对于对错、真实的矛盾,这是第四重矛盾。在对抗运动中,身处陆地的人不是理想的,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寻求自己的利益。原本怀抱热情追随、投入大革命的柯西莫,以为迎来的会是一个君主立宪时代,但未曾料想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的专政、独裁统治,最终在入侵沙俄中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柯西莫的争斗不为自己的利益,但一次次的投入、献身让他感到这其中充满着矛盾,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种思想是无懈可击的,没有一种形态时无可挑剔的,不论是启蒙思想的理性、大革命的平等、还是雅各宾政权的激进、法国共济会的反对天主教、各类伟大的思想家……缺乏独立思考、盲目投入的理想终会变形。卡尔维诺创造的新世界里,他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某种更上层的理想和为之的付出,他总是作为旁观者看一切,陆地上的哪一方都是不可信的、都不可能是绝对理想的,无论追随哪一方,都会从热情、反叛、真诚落入残缺、矛盾、迷茫、甚至否认,丧失着最初的盲目和笃信,理想的热情也就消散了。
沙俄将军曾说:“我把一件可恨的事情尽我们之所能做好了。这场战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我根本无法解释的理想……”柯西莫回答道:“我也是。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
生活在树上,是他在一种生活方式里选择了不合常规的、但真实、自我的。“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在个性被抹杀、行为被预定的统一范式里,不仅仅是自我部分的丧失,而是全部的丧失。虽然柯西莫的例子显得天马行空,但他不仅自己特立独行,也希望号召所有人可以独立、自由的生活。这一行为理应警醒不同阶段的人们,比如随着现代互联网大数据的兴起,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观点反而越来越狭窄、同质,面临信息茧房的禁锢,片面化、碎片化袭来,如何不被信息裹挟,保持自我思考、看清全貌是我们应该寻求和坚守的“顽固”。
我常常羡慕那些能够很强烈地、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人,而我是一个会从两面、三面……去旁观这个问题的人,于是,我总能得出很多种不同、但都能够被解释的态度,所以我变得矛盾且不明确,以至于更多时候我是含糊不清的。不管是柯西莫的热情投入,还是我的含糊犹豫,似乎都在说:自己才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自己的观点可能是落后的、有失偏颇的、“虚假的”,但也只有它是坚定的、义无反顾的、“正确的”。这里当然不是提倡唯我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说,作品背后正值冷战的紧张和迷失,作品恰恰是卡尔维诺的宣泄和思考:人们需要一些可以坚信、可以寄托的东西,他号召真实自我的回归,甚至是真实自我的完整回归,并在作品中袒露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人的主体性、独立和自由,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的关键。这样,才能达到所谓非个人主义的完整,即全社会、全人类、乃至全世界的完整。
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卡尔维诺的人称使用很有意思,第一人称“我”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纠正讲述时的完全客观和冷静。《树上的男爵》里的“我”是柯西莫的兄弟,稳重而通情达理,与柯西莫的性格恰恰相反,纠正作者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种写作手法也被称作第一人称越位叙事,它偏离常规第一人称叙事的既定航道,取道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从而在弥补第一人称叙事感知受限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新的人称叙事运用范例。卡尔维诺正是通过“我”的隐退与边缘化,才能使那个未被时代所裹挟的自由个体柯西莫出场,才能使现代社会个体生存危机得以被洞察。
四、树上和树下
尽管可以在小说中窥见政治元素,但卡尔维诺在政治立场上是包容的,可以说是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作家。时代背景、政治这些外部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卡尔维诺却以独特、奇妙的写作手法或批判或反映着现实,因此也被称为“新现实主义”作家。书中的柯西莫以独有的视角观察世界,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世界。组建消防队、袭击海盗、灭狼、领导反对什一税的抗争,他通过这些活动实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责任与价值。对于现实中的卡尔维诺而言,则是通过写书来实现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传递思考和感悟、宣泄和警醒。柯希莫因反抗父权而上树,最终又与父亲和解;卡尔维诺则是与社会和解,保持距离但仍以某种方式影响着它。
“树上”与“树下”的矛盾构成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距离,但它们也有着强烈的联系。《树上的男爵》告诉人们怎样找到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怎样在矛盾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如何在人生的洪流里进退自如。当然,现实的我们也无法做到爬到树上生活,书背后的时代已然过去,他的故事被看作是一段传奇,但树下的我和我们对于理想,从来也不是站在树上来旁观的,它一定是代表自己的,站在陆地上的,无论对错,无论是否矛盾。真正需要的不是重新建立一个世界,而是在身处的世界之上自建一种自洽和秩序。像柯西莫一样,拥有对生活的信仰,以及追寻自由、承担自由的勇气,这些本身就构成了生活的意义。书中的柯西莫在一生里遇到了各种矛盾,也有他身上体现出的矛盾,这可能是由于他的特殊视角和身份,也或许每一个人在一生里都会如此。所以,勇敢、坦诚地认识自我、接受自我、并以此完善自我——它既有求真求美的理想,又有乖戾反叛的冲动。饱有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投身生活、信仰、世界。同时,敬畏历史进程中的“现实柯西莫”,他们是是柏拉图、哥白尼、卢梭、伏尔泰、胡适……虽然他们不被同时代的人们理解,但是他们敢于坚持理想,用生命的热情点燃启蒙的火炬,引导和提升人类文明。
柯西莫反抗世俗,却不厌世,保持距离是为了“与他人真正的在一起”,是为了“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天空似乎永远遥不可及,就像书中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人类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轰轰烈烈的掀起革命,以崇高的理想开始,最后却以动乱和专制结束。但男爵在生命弥留之际的纵身一跃,归于苍穹,或许代表了卡尔维诺的愿望:忠于理想,面对现实,永不放弃。这个世界不完美,但它值得我们去为其献身。
“柯希莫·皮奥瓦斯·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匡时书院2023级数字经济实验班 李欣雨
阅读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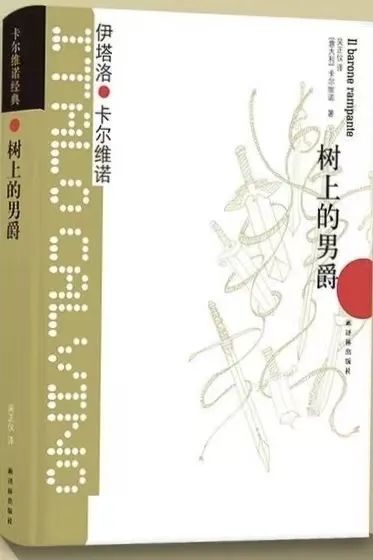
《树上的男爵》
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信息:2012/译林出版社
常感矛盾和迷茫的我们如何走向自我完整?卡尔维诺用精巧的想象和轻盈的描绘,创作出《树上的男爵》,在真实和幻想的边界,与树下的我们共同思考、引发共鸣,鼓励我们去建立属于自己的自洽和秩序。
作者:匡时书院2023级数字经济实验班 李欣雨
